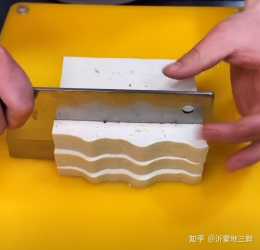我那遠去的老院子
突然想起,又有好久沒回鄉下老家了。倒不是因為忙,就是沒事的時候,也找不出回去的理由。
老家在農村,老房子還在,不過好久沒人住了。我知道我依然還是個鄉下人,比外地的鄉下人又好一些,是個當地的鄉下人。
進縣城教書近二十年了,一點沒有感覺到自己是個城裡人。說著方言,穿著落伍的衣服,不修邊幅,不敢大聲地說話,走路嚴格走在人行道的一側,害怕紅燈和黃燈,站在十字路口,有時候不知道朝哪兒去,一個十足的鄉下人。
老家的院子還在,大門還在,然而幾面牆卻早已倒掉了,露出犬牙交錯的屋脊樑頭。時常有野貓從殘破的牆頭間來回穿梭。
老家的院子很大,原先在院子裡栽了許多樹。前面是葉小果大的棗樹,往西是一株銀杏樹,再往南的牆頭邊栽了兩株水杉,這幾棵樹都在壓水井的排水經過的地方,因此棗樹異常的能結果實,銀杏樹葉綠枝挺,兩株水杉樹更是直入雲霄。
院子的東側是兩間廚房,西側仍然是樹和花。有人忌諱院子裡有樹,說那是“困”,然而我不相信。如果那樣的話,院子裡還不能有人呢,那不是一個“囚”嗎?
磚頭鋪的小路旁有一棵梨樹,那是我和父親嫁接而成的。原先這是一枝普通的可嫁接果樹的樹,冬去春來的時候,我們到西廠的梨園裡剪了幾枝酥梨和明月梨,把它們的芽孢嫁接到那株小樹上。
三四年後,梨樹開花時,有白的和黃的花。每到月半之時,梨花院落溶溶月,很有詩意。掛果之時,更是一番景象,低垂的枝頭上掛滿了深青色的酥梨和暗黃色的明月梨,微風拂過,竟能聽到彼此的碰撞聲呢。
梨樹的西南有一株石榴樹,在銀杏的北面。每到中秋前後,掛滿枝頭的石榴,漸漸地裂開了嘴,露出通紅的石榴籽來。
往北面去,留了一片空地,那是母親的菜地。面積不大,讓母親料理得很有用,夏天長得老長的黃瓜,爬滿牆頭的絲瓜,還有秋天的梅豆,晃盪在架下的吊瓜 ,總能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再往北,是通往屋後的巷道,巷道口是一株健壯的百日紅,也叫鳳凰花。每年從春天一直開到秋天,紅豔豔茂密的花簇把西邊的天空裝點得火熱奔放。
堂屋是起脊的,屋脊用的就是原來栽的水杉。原先水路上有四棵,兩棵大的筆直的做了堂屋的屋脊,一探三間還有剩餘,因此做了棟樑。堂屋是我工作後兩年才蓋的,主要是結婚用,原先的三間土屋倒了一間。真的是兩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蓋新房是件大事,忙碌了一年多,新房蓋好,新娘也到家了。
院子裡漸漸地人多了起來,很快兒女們也能拿竹竿攆雀打棗了,整日裡院裡院外盡是大人和孩子穿梭的身影。那時的堂屋我們住,大門是父母住,小院春夏秋冬果實累累,一片盎然。弟弟在外地工作,不常回來。姐姐就在附近,離我家不遠,常來,外甥很多時候都在咱家,主要有小孩一塊玩。
千禧年後,我從省教院學習回來,又在農村工作了一年,一個偶然的機會被借用到一中,後來借調,再後來,和原來的單位幾乎沒有了關係。
然後,孩子們和我一道也離開了老家的院子,從小學讀到了高中,現在也離開我們,開始他們的大學生活。
又幾年,弟弟也成家有了兒女,父母也離開了老家的院子。從此老家的堂屋鎖上了,大門也鎖上了。一年只有偶爾幾次回去看看,打掃打掃,每次回去都會發現院子裡草長蟲飛。
有一年的春天,家裡的一個潑皮無事的爺爺,撬開老院子的大門,把那棵開的正豔的百日紅給偷偷地賣了,據說賣了幾百元錢,很快又被他喝掉和賭掉了。
後來,那棵棗樹也莫名其妙地乾枯,成為一株死樹。梨樹每年還在結果子,只是越來越小了。
大門東面那棵香椿樹似乎也不見了,門口兩旁的兩株杏樹根本長成不了杏子,就沒了果實,被玩耍的孩童敲了去。再往前的那株柿樹基本上就沒見過柿子。最前面靠近公路的兩棵大楊柳樹,因為門口修路擴建,前幾年也挖掉了。
偶爾回老家有事,從公路邊經過,遠望歪倒掉的大門,或者進去駐足片刻,撫摸還堅守自己位置的梨樹、銀杏和石榴樹,它們竟然也有些老了。我們不在家的時候,老屋,院子,樹,甚至是無名的草,它們互相鼓勵和安慰,守著逝去的日子。
老院子,在漸漸地遠去。我們和父母都很少回去了,只能任憑它的頹圮和破敗。有時候還能在夢中偶爾出現,而我的兒女們很小就離開了老家,離開了那個老院子,老家的印象可能是模糊的,甚至沒有了一絲痕跡,他們還有老家嗎?
我們還有老家嗎?
那屋,已經頹圮;
那樹,也已老去;
那蝴蝶,還能款款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