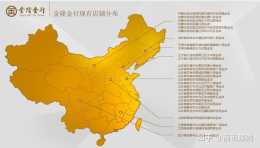閱讀筆記 | 張愛玲——在誇張的城裡栽跟頭
筆記整理於2017.12.1

大四還讀書就挺可怕的,大四還讀了張愛玲,莫不是這家子得了失心瘋?
我挺懼怕張愛玲的。年少不讀書,只一味覺得再沒有誰的名字矯揉似這三個字。淑女、文質彬彬的中文系女生適合讀她,我係乖張,相比情愛,更該偏執於歷史、當下和未來——這愚鈍和刻板一定不只存在在之前的我身上。
坊間這句“年少不懂張愛玲,讀懂已是不惑年”其實是可笑的。在我這,這句話當這樣講:年少只聞張愛玲,不讀偏說不懂她。
十七歲,她寫完《霸王別姬》,二十三歲,她作畢《傾城之戀》、《金鎖記》。有人咋呼四十歲還不懂張愛玲的字,卻不知這女人造就那些“難懂之字”時才剛過二十歲,這就是人們咋呼著四十還讀不懂的人——如今讓那些年過四十的人來仰視當下某位思想傑出的青年,就不知要儲備他們多少的自知和謙遜了。
如今我還是挺懼怕張愛玲的,為何?因為透徹。人事本就複雜,可張能剖析人事,並將人們沉迷的、疑惑的、不願承認的,統統撕開來,露出裡面的瓤。她把世俗變成極致的浪漫,卻又把極致的浪漫消化成最後的渣滓。世間道理生冷得很,撕破並不意味著能超脫,但起碼知道,那就好。
這一期的筆記來自小說,不知情節無關大痛癢,我將只列舊時代裡那些燃燒過後赤裸的渣滓。但願不要有人怪我毀壞憧憬,因為憧憬是毀不掉的。張愛玲做不到因為透徹而失掉憧憬,放心,大部分你我也做不到的。

1 《紅玫瑰與白玫瑰》 出版於24歲·振保的生命裡有兩個女人,他說一個是他的白玫瑰,一個是他的紅玫瑰。一個是聖潔的妻,一個是熱烈的情婦——普通人向來是這樣把節烈兩個字分開來講的。·也許每一個男子全都有過這樣的兩個女人,至少兩個。娶了紅玫瑰,久而久之,紅的變了牆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還是“床前明月光”;娶了那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飯粘子,紅的卻是心口上的一顆硃砂痣。·嫖,不怕飄得下流,隨便,骯髒黯敗。2 《傾城之戀》 出版於23歲·徐太太道:“年紀輕輕的人,不怕沒有活路。”白流蘇:“有活路,我早走了!我又沒念過兩句書,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能做什麼事?”徐太太:“找事,都是假的,還是找個人是真的。”流蘇:“那怕不行,我這一輩子早完了。”徐太太:“這句話,只有有錢的人,不愁吃、不愁穿,才有資格說。沒錢的人,要完也完不了哇!你就是剃了頭髮當姑子去,化個緣吧,也還是塵緣——離不了人!”·流蘇交叉著胳膊,抱住她自己的頸項。七八年一眨眼就過去了。你年輕麼?不要緊,過兩年就老了。這裡,青春是不稀罕的。他們有的是青春——孩子一個個被生出來,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紅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來,眼睛鈍了,人鈍了,下一代又生出來了。這一代便被吸到硃紅灑金的輝煌背景裡去,一點一點的淡金便是從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那是個火辣辣的下午,望過去最觸目的便是碼頭上圍列著的巨型廣告牌,紅的,橘紅的,粉紅的,倒映在綠油油的海水裡,一條條,一抹抹刺激性的犯衝的色素,竄上竄下,在水底廝殺得異常熱鬧,流蘇想著,在這誇張的城裡,就是栽個跟頭,只怕也比別處痛些。(香港)·柳原道:“一般的男人,喜歡把好女人教壞了,又喜歡感化壞的女人,使她變為好女人。我可不像那麼沒事找事做,我認為好女人還是老實些的好。”流蘇瞟了他一眼道:“你以為你跟別人不同麼?我看你也是一樣的自私。”柳原笑道:“怎樣自私?”流蘇心裡想著:你最高的理想是一個冰清玉潔又富有挑逗性的女人。冰清玉潔,是對於他人。挑逗,是對於你自己。如果我是一個徹底的好女人,你根本就不會注意到我。她向他偏著頭笑道:“你要我在旁人面前做一個好女人,在你面前做一個壞女人。”柳原想了一想道:“不懂。”流蘇又解釋道:“你要我對別人壞,唯獨對你好。”柳原笑道:“怎麼又顛倒過來了?越發把人家攪糊塗了!”他又沉吟了一會道:“你這話不對。”流蘇笑道:“哦,你懂了。”柳原道:“你好也罷,壞也罷,我不要你改變。”·你如果認識從前的我,也許你會原諒現在的我。·柳原:“我自己也不懂得我自己——可是我要你懂得我!我要你懂得我!”他嘴裡這麼說著,心裡早已絕望了,然而他還是固執地,哀懇似的說著:“我要你懂得我!”流蘇自己也忖量著,原來範柳原是講究精神戀愛的,她倒也贊成,因為精神戀愛的結果永遠是結婚,而肉體之愛往往就停留在某一階段,很少結婚的希望。·柳原搖頭道:“一個不吃醋的女人,多少有些病態。”·夢是心頭想。·“本來,一個女人上了男人的當,就該死;女人給當給男人上,那更是淫婦;如果一個女人想給當給男人上而失敗了,反而上了人家的當,那是雙料的淫惡,殺了她也還汙了刀。”·近三十的女人,往往有著反常的嬌嫩,一轉眼就憔悴了。·柳原笑道:“我們那時候太忙著談戀愛了,哪裡還有工夫戀愛?”

3 《金鎖記》出版於23歲·三十年前的上海,一個有月亮的晚上……我們也許沒趕上看見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輕的人想著三十年前的月亮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溼暈,像朵雲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陳舊而迷糊。老年人回憶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歡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圓,白;然而隔著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帶點淒涼。·敝舊的太陽瀰漫在空氣裡像金的灰塵,微微嗆人的金灰,揉進眼睛裡去,昏昏的。街上小販遙遙搖著撥浪鼓,那瞢騰的“不楞登……不楞登”裡面有無數老去的孩子們的回憶。·他不是個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裝糊塗,就得容忍他的壞。她為什麼要戳穿他?人生在世,還不就是那麼一回事?歸根究底,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
短些好。結尾我單拿出這一段:
那是個火辣辣的下午,望過去最觸目的便是碼頭上圍列著的巨型廣告牌,紅的,橘紅的,粉紅的,倒映在綠油油的海水裡,一條條,一抹抹刺激性的犯衝的色素,竄上竄下,在水底廝殺得異常熱鬧。流蘇想著,在這誇張的城裡,就是栽個跟頭,只怕也比別處痛些。(香港)
關於這一段,七十年前七十年後,同樣適用。七十年多前的香港陷落了,可七十年後,這座城還是一派繁華喧鬧。舊時的香港和如今的香港,和北京,和上海,和廣州、深圳又有何不同,人們削尖了腦袋湧進去,在“不可理喻的世界裡”掙扎欲締造一段自己的傳奇。
這也像遊戲“吃雞”,人們落在一個島上,為了活到最後而奔走。有的人剛擇了個良處跳下傘,連個頭盔還沒撿到,就被人一槍崩出局;有的人技術精尖,揹包充實,一槍一槍殺了人走到最小的圈子裡;也有的人打一開始就落在了最偏遠荒涼的地方,運氣好的,撿撿裝備追追白圈,咔,活到了最後。
良禽擇木而棲?上海也好,香港也好,荒島房屋密集的地方也好,偏遠到聽不見槍聲的荒野也好,在哪裡栽跟頭不痛呢?何況這又是個人人誇張的時候。我不知道明兒個我將去向哪裡,但總歸記得去到那裡都要做好栽跟頭的準備,但今兒,我不也還在跟頭裡嗎?
最後,我要說的是——
色素啊色素!七十年前人家都能看出香港廣告牌紅黃撞色的醜,怎的七十年後大街上還是密佈三原色?審美啊審美!人要有進步的啊!設計們請多一些積累和堅持;甲方們,請慎重要求設計加顏色、標誌和口號。
如果王嘉爾好聽的Hip-hop廣告歌(V)ision,最後沒有加那句違和而詭異的“逆光也清晰,照亮你的美”,傳播輻射我猜會有不同:)
謄自個人公號:溫迪精內容 | 張愛玲《金鎖記》《傾城之戀》《紅玫瑰與白玫瑰》Pictures | 電影《傾城之戀》Instagram | junl_x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