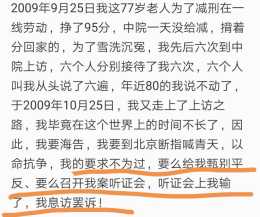曹寇:南京有個八卦洲
曹寇,70後作家。生長於南京,也寫南京,但他的表達方式,寫作的地理空間,和葉兆言、韓東、畢飛宇這些著名的“南京作家”完全不同。
比如他作品的名字:《割稻子的人總要彎腰駝背》、《朝什麼方向走都是磚頭》、《能幫我把這袋垃圾帶下樓扔了嗎》、《攜王奎向張亮致敬》……他說小說的標題既是文字的整體內容之一,也是獨立文字。
他從不寫“六朝古都”,不提“金陵王氣”,他的故事都發生在葫蘆鄉、塘村、鴨鎮……這一類非城市的鄉野之地,它們是他生活過三十年的八卦洲的化身。而不同小說裡反覆出現的張德貴、張亮、王奎、高敏、李峰……這些人物,是他在八卦洲時,生活裡所見人物的提煉。
長江從上游的西部一路東來,經過安徽,進入江蘇,抵達南京,將南京切分成江北、江南兩部分,並在江上留下幾個沙洲,八卦洲最大。曹寇的祖輩也是沿著這樣的路線遷徙,從安徽沿江而下,遇到八卦洲,就留下了。因為立於江中,使它在地理上、文化上,懸垂於江北、江南之外,成為一塊被遺忘的飛地,直到曹寇的出現。
然而曹寇構建的世界也不使人愉悅,他筆下的鄉村,既非精神家園,也非桃花源,文字裡的人生大多無聊、頹喪、絕望。
合上書本,想象地圖上的八卦洲,會對這個之前在南京的寫作裡從未出現過的地方充滿想象,也略生怯意:真的要找他聊一聊嗎?
要的!因為他,我們在南京的版圖才擴充套件至八卦洲。還因為在他貌似無聊的人生裡,不時閃著金光:他喜歡汪曾祺,喜歡他在《道具樹》裡寫,在樹下看書,“感覺有清新空氣流動”;他還喜歡孫犁,喜歡他在《荷花澱》裡寫妻子坐在月光下編織竹蓆,不一會兒她的身下就是一大片,她像坐在雪地裡,又像坐在一片雲彩裡……他也寫不那麼滿意的家鄉,小時候,父親帶他和哥哥去很遠的地方搞魚摸蝦,“回來的路上,巨大的斜陽懸掛在垂死的柳樹梢頭,螢火蟲與星光幾乎同時出現。我們一路上捉了很多螢火蟲,到了家門前,才鬆開手掌。無數的螢火蟲環繞在周圍,有如行走在太空中一般。”明亮、溫暖而美好。
那天細雨霏霏,先去邁皋橋的紅山街道,他城裡的家中。周圍的街道、天橋、夜店,常出現在他書裡,記錄了他從島上初來城裡時的生存空間和心理路徑。然後,我們一起乘公車,經過他上大學時的師範,經過改變他命運的南京長江二橋,回到他在八卦洲鄉下的老家。
在洲上,他用電瓶車載著我四處溜達:他曾經教過書的中橋中學;每年夏天洪水氾濫時,他去看熱鬧的堤壩(圩),堤壩有內、外兩道,之間還有大片田地和白楊樹林,風吹過白楊林時,聲音如海潮……因為下雨,道路泥濘,很多地方只能下車來推著走路,後來索性放棄,直接走路。
我們穿過田間阡陌,穿過家家門口都有碼頭的河道,穿過他和哥哥正在蓋新房子的宅基地。洲上河汊縱橫,路旁雜樹生花,地裡小麥金黃,彌眼的白楊和水杉。過橋時,會頻頻停下來駐足觀望,多麼桃花源的鄉野,多像精神家園!為什麼他書裡盡是頹喪之氣?
經過一段林中小道時,我怯怯地問:你常有虛無感嗎?他說“虛無”不是一種感,是存在本身。再次跨過長江二橋,回到城區時,遠遠看見一大片密密麻麻、一模一樣的高層樓房,四周沒有山,沒有樹,就那樣兀自挺立著,像某個外星球留下的遺蹟。他指著它們說:“你看,這是為那些剛畢業就結婚的大學生們準備的,雙方家裡拿出一輩子積蓄付個首付,然後兩人一起還房貸,直到孩子長大成人,又重複一樣的命運……這還不虛無?”
在那段林中小道,我又問:假使人生本質是虛無,為什麼不寫下那些美好的瞬間來支撐我們度過虛無,而是寫下虛無,使我們更覺虛無?他說是的,前者如汪曾祺,所以他很偉大,也很感人,“一個人莫名其妙的來到這個世界,莫名其妙的做著一些自以為是的事,它們到底是真相還是幻影?我能做的,只是寫下現實。雞零狗碎,一個人的生活真相無非如此。”

▲見曹寇前,看過他很多篇訪談。每多讀一篇,去見他的勇氣就減少一分。後來見面後,他笑著說,“以前和記者很多抗爭”。他小說裡的氛圍,和訪談一樣,多有抗爭,但臨行前看完他兩本散文集:《生活片》和《我的骷髏》,忽然發現了另外一個曹寇:野生而溫柔。在這兩本散文集裡,他詳實交待了他的生存環境,過去四十年的生活軌跡,和每一段軌跡裡,他和周邊環境,周邊親友的關係。我想問的問題,他早已寫在書裡。這篇“訪談”裡的回答,大多摘抄自他書中。那天和他回八卦洲的整個下午,只是默默尾隨在他身後,確認這“野生而溫柔”的現實來源而已。
行李&曹寇
1.
行李:坦白說,我是學地理的,也來過南京多次,但是很慚愧,因為看你的書,我才第一次知道八卦洲。我念大學時在長沙,那時常夜騎去橘子洲頭遊玩,雖然和河東河西各自只隔了數百米的江水,但感覺像孤島,自由和孤獨同在。不知道八卦洲是怎樣的?
曹寇:八卦洲是南京城北長江中的沙洲,四面環江,長期與世隔絕,加之多為外省移民,和近在咫尺的南京完全屬於兩種語境。洲上原來是沒有人類居住的,直到大約100年前,清末民初,災難,戰禍,導致大量難民,他們順江而下,找到了這麼一片“處女地”,開荒種地,繁衍至今。
行李:那你的祖上來自哪裡?
曹寇:安徽廬江,《孔雀東南飛》說的就是那裡的故事。祖父母活著的時候,總是稱安徽廬江的老家為“上江”,他們苦於戰亂和飢餓,以逃荒者的身份背井離鄉尋找生機。那時八卦洲人煙稀少,遍地蘆葦,汛期消失,旱季凸顯,正在等待他們趕來墾荒和防洪,有如命中註定。
現在八卦洲上,五分之三是安徽人,有些村子全是安徽人,相當於安徽的某個村莊被連根拔起,整體移植到了八卦洲。那裡的語言與南京不同,民風、民俗也不同。我小時候,常常有安徽的戲班子來洲上唱戲,一唱就是一兩個月,很多老人會去聽。後來我寫過一篇《八卦洲人口傳略》的,將洲上人口分為安徽、六合和南京三股移民,因為它在行政上屬於南京的棲霞區,又與江北的六合區隔岸相望。
行李:洲上的自然環境是怎樣的?
曹寇:很多河,很多塘,在長江下游嘛,每年夏天都生活在即將被淹沒的恐懼中。1983年,洪水滔天,當時我6歲,被政府組織和其他兒童及老年人先行撤退,前往市區避難。一路上我們看到無數奔往碼頭的拖拉機,也看到每家每戶門前的水上都紮了棚屋,你知道棚屋嗎?一種高於屋頂,在幾棵樹上搭建的簡陋房子。棚屋裡堆著傢俱和棉絮,一旦破圩(堤),洪水洶湧而至,大人們就會迅速爬上去,在樹上生活。
行李:後來呢?真的在棚屋裡生活,棚屋下洪水滔天?
曹寇:多麼遺憾(在當時的我看來),那年沒有破圩,棚屋沒有用上。許多被搬上去又被搬下來的傢俱經過一個夏天的雨淋日曬,不少都壞了。所以人們也懶得拆除它們,於是給兒童們提供了新的世界。我哥哥每天一放學就爬上去,在上面寫作業,飯也不下來吃,叫我把飯碗放進籃子裡,他用繩子吊上去。我因為太小,很難上去。後來上去過幾次,第一次看到了自己家的屋頂,上面有幾顆牙齒,應該是姐姐和哥哥們換牙齒的時候,奉母命扔上去的下排牙。
行李:那場景在一個小孩子的眼裡,有些浪漫,有些荒誕。
曹寇:我家有一頭牛,小時候去放牛時,為了使放牛更像一幅畫,我請求父親在集市上給我買一根笛子。我的笛聲使過路的鳥雀停在空中,它們站在雲端側耳傾聽的樣子至今讓我感動。據說它們希望從我優美的笛聲中汲取點音樂細胞,好讓自己叫得更動人。後來聽了牛郎織女的故事,我就不吹笛子了,專門沿河岸走,我以為從我們生產隊走到另一個生產隊,就會遇見一群在河裡洗澡的仙女……當時覺得八卦洲真大呀,就是我的整個世界。
行李:現在回首,真是燦爛而寂靜的童年呀!
曹寇:是的,很寂靜。我家旁邊有一叢竹林,還有一棵生長了二十多年的泡桐,我房間的窗戶就對著它。那時回家沒事幹,只一味地站在窗前發呆,不知道該乾點什麼。泡桐樹開花,然後落掉,香氣嗆人,讓人傷春。夏天的大雨擊打在寬大的葉片上,發出響亮的聲音,此起彼伏,但是覺得寂靜。我年復一年地站在窗前看著它,然後低下頭在我那張破桌子上寫毛筆字,或者讀點古代的書。有月亮的夜晚,我會開了後門走出來,在泡桐樹蔭下走幾圈。月光明亮,竹林、樹蔭顯得陰翳,塘裡不時傳來魚躍和氣泡的聲音。街道上的狗都是熟識的,隻立在月光下愣愣地看我幾眼……後來與朋友們聊起家鄉,我總會提到泡桐樹,提到樹蔭下那段與世隔絕的時光。
行李:你還在洲上的中橋中學教過書,那時學校如何?
曹寇:春天的時候,渠邊和田埂上都長滿野菜,薺菜花細小緊密,像一層薄雪點綴在綠野之中。菜花可以開到視窗,安靜的下午,教室裡能聽到豆莢噼啪爆裂的聲音,一個一個又一個。還有環繞校園的灌溉渠,清水長流,有青蛙叫,有大蝦朝我們張牙舞爪。經常有學生逃課去釣蝦,我逮過幾次,但從來沒有沒收,於是他們的蝦經常爬出課桌抽屜,爬得滿地都是。有次一隻大蝦爬到了講臺上,我沒在意,“喀嚓”一腳把它踩死了……學生們都噓氣,我也覺得自己犯了罪。
行李:那時洲上進出的交通如何呢?
曹寇:都要坐船,洲上有三個碼頭。記得小時候學校組織去南京春遊,先是集中到學校,學校僱一手扶拖拉機,把我們拖到碼頭,上船,過江,再坐車。過江時最常見的場面是:一個鄉村大姑娘為了過江進城,打扮得乾乾淨淨,穿一身廉價且有摺痕的新衣。她在城裡晃了一天,因為暈車吐得一塌糊塗,最後以衣衫凌亂,鞋子上佈滿陌生人腳印的可笑形象回到家園。
行李:所以你不謳歌鄉村,也不喜歡看人謳歌鄉村。
曹寇:歌唱鄉村,歌唱往昔,歌唱貧窮,這幾乎是當代抒情的正規化。鄉村從來就不是我的精神家園,亦非“故鄉”。它只是我曾經居住過的地方而已。而所謂往昔,除了不堪回首,除了永不再返,還剩下什麼?
行李:後來回去過廬江嗎?
曹寇:祖父和父親生前多次提議要回去一趟,但至死也沒成行。後來陰差陽錯,我居然跟著一隊人馬以旅遊者的身份重返故里。當地的貧窮完全破壞了我的想象。遍地是不倫不類的建築和神情木納的人類,此外就是垃圾。我當時被安置在一片農田中央的度假村,因為四周都是農田,我注意到傍晚時分有水牛被人牽著在田埂上走,一條黃狗在前面奔跑。晚上我躺在酒店床上的時候,輾轉反側,然後就產生了幻覺,我懷疑我那早已死掉的祖父、祖母和父親並沒有死去,而是以死亡為藉口或途徑,回到了故鄉。此時此刻,他們就在我置身的度假村四周的農田裡彎腰勞作,或者正和那條黃狗在泥地裡翻滾,他們攢錢買來的那頭牛也正站在田埂上低頭吃草。
2.
行李:你祖上何時移居到八卦洲的?
曹寇:大約20世紀40年代,祖父攜妻兒從安徽廬江遷到南京,投奔一位叫趙子園的本家叔伯。趙子園是地主,我祖父當過他的管家,並獲贈幾十畝地,但很快就被祖父敗掉了,祖母說,全部扔進了秦淮河的青樓裡……祖母也是個糟糕的農村婦女,和祖父一起生了四個兒女,只胡亂養活了兩個,我爸和我二爺。
行李:你父親是個怎樣的人?
曹寇:父親生於1941年,解放前給地主家放過牛。從六十年代開始,他先後做生產隊計工員、會計、大隊會計。八十年代,做村服裝廠、鐵鑄廠、鄉供銷社、糧站會計。九十年代,先後做過木器加工廠、電燈泡廠,及各種鄉鎮企業、民辦企業及校辦企業的會計。然後是死。
在鄉人的認識裡,我的父親是個正直、忠厚的人。他下葬那天,暖穴使用的,除了草紙,就是他的帳簿,書寫工整、一絲不苟。我曾經保留一本六十年代的黑皮軟面抄本的帳簿,裡面記載了那個年月村裡勞動力每天的勞動情況。
行李:他一個人就是一個時代呀。
曹寇:父親是個疏於農活而熱衷於手工的人,經常是母親在地裡揮汗如雨,他卻在家裡自制麻將牌和風箏什麼的。他愛喝酒,喜歡自己製作下酒菜。在春夏季節,會扛上網,叫我背上竹簍跟他去捕魚蝦。
我們從門前的河汊開始,會走到在當時的我看來很遠很遠的地方。那些遠地方無比荒涼,只有田地和雜草叢生的河水,卻魚蝦繁茂。有時他會脫掉衣服下河去摸,摸著摸著,就一個猛子扎到河底,半天也不出來,連他攪動的浪花也逐漸平息。這時,我聽到四周無邊的寂靜,會感到害怕,然後大喊他。後來,天就黑了,在那些荒涼的地方,總隔三岔五地生長著一些老氣橫秋的柳樹,我至今能記起太陽在柳樹上慢慢落下的場景,多麼巨大的太陽啊,鮮紅無比!
我們開始朝家的方向走去,等到家,天已經黑透,竹簍裡滿載著魚蝦,我也已經背不動了。哥哥也去的話,就跟我用根樹棍抬著魚簍。我們還會捕捉許多螢火蟲,等到家門口,就把它們放掉,幾十幾百顆螢火蟲頓時炸開,縈繞在我們周圍,就像我們行走在太空中一樣。
行李:這樣的父親,當時也許叫你感情複雜,但以今天城市孩子的眼光看來,這樣的父親多好!
曹寇:是,他給我們的已經無比豐富。
行李:你在文學上有啟蒙老師嗎?
曹寇:有的。我有七個舅舅,其中六個是農民兼手藝人,唯有大舅在城裡,是個文化人,先是寫小說,然後去出版社編書。我最早的閱讀,得益於他每次回鄉帶的書。還有二爺,一度是個文學青年,後來成了小學老師,直接教我,對我影響很大。以及我大姐,她是80年代中晚期的高考落榜生。那是一個以文學和詩歌作為青年時尚的時代,我看過大姐和她的同學們爭搶書本的場景,和她們的詩歌抄本。
行李:和你一起抬魚蝦,一起抓螢火蟲的哥哥呢,對你影響大嗎?
曹寇:小時候總是和哥哥一起幹活兒,比如半夜醒來,迅速穿好衣服,吃完麵條,推上裝著兩簍蔬菜的腳踏車,一前一後上車出門,趕在頭班船之前到碼頭,登船過江,挑一家有空位的農貿市場,在天黑之前將三四百斤蔬菜一斤斤賣掉……多年以後,我和哥哥早已擺脫了這種生活,並且搬離了八卦洲,在南京買了房。但我們並不住在一起,走動也不頻繁。
老實說,年月變化已使我們無話可說。只有每年清明,八卦洲油菜花盛開的時節,回鄉給父親上墳,才找到一些共同話題。我們並肩而行,以兄弟二人的名義和村裡的人打招呼,此時往事歷歷在目。想起父親去世時,正值大雪,喪事辦完後,我和哥哥坐在屋子裡相對無言。想到平日裡父親總是以筆直坐在腳踏車上的形象準時劃過我們的視窗,哥哥不禁哭了起來。我一下子不知所措,然後下意識地抬起胳膊拍打了一下他的脊背……
行李:沒想到父親成了你們的橋樑。
曹寇:我和哥哥受到父親許多影響,吹笛子拉胡琴,抽菸喝茶,以及聽單田芳。他喜歡收聽廣播書場,劉蘭芳、袁闊成和單田芳輪番上陣,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在我印象裡,單田芳居多,這人聲音沙啞,感覺很老,書卻說得特別生動。
那些年,父親、哥哥和我幾乎每天都會準時收聽單田芳。總是午飯或晚飯結束的時間,其時,碗筷已收,桌子被母親擦淨,散發著幽暗的光線,還殘存著一些飯菜的溫度和香氣,收音機就放在桌子中央。我們或坐在桌邊,或靠在糧食麻袋上,或蹲於門檻……也許和此時胃中的食物有關,這個場景下,我總是能夠感到某種幸福,現在回想起來,仍然感同身受。
父親死於1996年。後來我抽菸喝茶成癮,卻已忘掉了吹笛子,也忘掉了聽單田芳。有天在網上下載了單田芳的幾部書,關了燈,睡在床上聽。單田芳還是那麼精彩,那麼老,聽得我熱淚盈眶。好幾次我都恍惚地有個感覺:單田芳正是我已死去多年的父親。
3.
行李:什麼時候離開八卦洲,真正進入“南京城”?
曹寇:18歲時,進城讀書。那之前,只在名義上算一個南京人。八卦洲上多是移民,但是進城多年後,我發現南京城裡住著的,也沒什麼“南京人”。
行李:何出此言?
曹寇:作為一個流亡和過渡城市,南京在兩千年的中國歷史上一直充當著很不光彩的角色。它總是收留那些崩潰的中原政權,供其苟延殘喘。地處吳地,南京話卻完全不同於吳語,屬北方語系,這是拜那些中原逃難政權所賜,但幾乎所有在此定都的王朝都像個夭折的孩子那樣,在人間匆忙一啼,轉瞬寂然。南京就是一個被不斷屠城的地方,哪裡會有什麼老南京!
行李:婁燁拍《春風沉醉的夜晚》時,在南京取景很多。他鏡頭下的南京,有些曖昧、有些暗淡,影評人衛西諦形容為“灰綠色”,就是南京的色調。
曹寇:古城牆的色調天然黯淡,氣候上也是陰雨連綿,怎麼看都像一塊傷心地。老實說,談一場失敗的戀愛,此地絕佳。我也拿過關於南京的問題請教撰寫《老南京》的作家葉兆言,他說,南京於他而言,就是一個住了幾十年的窩,對我也是。
行李:但南京城似乎是孕育作家的沃土,這裡也有幾位影響過你的作家。
曹寇:是,這裡有楚塵創辦的“楚塵文化”,有使人眼前一亮的朱文,有韓東早期創辦的“斷裂”和“他們”文學網站。我,連同和我年紀相仿的在南京的作家,都深受他們影響,尤其韓東,我最初的小說,就是發表在“他們”的網站上。韓東特有的冷靜、節制、幽默(荒誕感),以及超撥於此的傷感和智慧,都極其迷人。
我們認識有15年了,他清瘦、沉穩、談吐不凡,毫無昏聵陳腐之氣,而且在生活上出了名的節制:每天早上六七點起床,從奧體家中坐地鐵到鼓樓,再步行至蘭園的工作室,以上班打卡的紀律來對待寫作。早些年週末,他還和朋友們一起爬爬紫金山,這兩年放棄運動,以打坐為主。他工作室有個香爐,每日打一炷香。他是講修養那一類人,修身修德修文,養生養命養道。人和作品渾然一體,相得益彰。
行李:聽說他對你評價也很高。
曹寇:那些都是虛的,倒是有一次他說我是典型的“偽惡”,讓我凜然一驚。
行李:“偽惡”,真是這樣。看你作品時,有點又愛又怕,因為看上去“惡”,所以怕,但知道是“偽惡”,所以愛。有你們這些人,南京城到底還是迷人的。
曹寇:南京這地方養人,但不發秧,想發秧的大多趕赴京滬這些名利資源豐富的地方找機會去了。在南京,如果你真的熱愛文藝,那就熱愛下去,要麼你就放棄,買份晚報過市井生活,也是儼然的幸福。
行李:你中間離開過南京去了廣州一年?
曹寇:是,記得是過完年坐火車過去。大雪,途經湖南時,大面積被雪壓斷的樹木和電線杆子觸目驚心。再之後,穿越南嶺的眾多隧道,當火車進入韶關境內時,烈日當天,明亮得我幾乎眼前一黑。葉片巨大的香蕉樹,身形高大的榕樹,像瘋了一樣在使勁綠使勁招搖,這裡竟然已經是春天!火車不僅穿越了空間,也穿越了時間。我想起曾經寫過一篇小說,標題叫:火車開往城春草木深。這不是抒情,而只是事實。
行李:是啊,一過南嶺,就是另一個世界,那裡和南京的差別,遠大於八卦洲和南京城的差別。為什麼要去廣州?
曹寇:因為我厭煩了在南京的生活。但我並沒有移居廣州、“混不好就不回來了”的打算。我對這句廣告詞深惡痛絕,它只是“衣錦還鄉”的口語方式。“混好”是為了“回來”炫耀的嗎?混好的人壓根就不應該“回來”。
行李:在廣州的生活如何?
曹寇:在南京時,我每天早上六點半就能起床,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樸生活。到廣州後,上午九點睡覺,黃昏時分起床,晚上工作和寫東西。廣州畢竟比南京喧囂,只有夜晚,最深的夜晚,才能恢復一定程度的平靜。
等到天灰濛濛地亮起來,那些不知來自何方的鳥鳴清脆、悅耳,使人想到“天籟之音”一類的詞。那時我會像剛起床的人那樣,沖涼、洗臉和刷牙,然後穿戴整齊,下樓去吃早飯。這時大街上開始有上班的人流,我們相遇,但大家都是陌生人,只是擦肩而過。我覺得這樣挺好。你必須明白,在芸芸眾生之中,你只是獨自一人,即便人口像災難一樣將你淹沒,陽光像災難一樣把你淹沒,時間像災難一樣把你淹沒,你仍然獨自一人。當然,與廣州無關。
4.
行李:你已經離開八卦洲,在南京城生活了十多年,現在回望八卦洲,它對你意味著什麼?
曹寇:八卦洲涵蓋了我三十歲前絕大部分的人生,對寫作來說,它給我提供了切實可感的“經驗”。它是我的生活,是原料,是可憐的人生經驗,也是自然而然。
行李:在你的生活裡,在你的書裡,八卦洲好像就意味著鄉村,但你對鄉村,有時深惡痛絕。
曹寇:我出生於農村,師範畢業後又返鄉教書,之後才進城買房定居。攏共算起來,我有近二十年的鄉村生活經驗。在某種意義上,鄉村生活是我最為重大的生命體驗。不知別人是否如此:進城十多年來,哪怕是在廣州飄著的那一年,乃至在德國待過的那一個月,睡夢中的景象仍大多是我熟悉的那個村莊及其相關人物。每次醒來,我一方面驚訝於鄉村在記憶(潛意識)中的不二位置,另一方面確實黯然神傷。鄉村於我如此重要,但我不僅不喜歡中國鄉村,也討厭將鄉村升格為“精神家園”,以及“鄉愁”、“近鄉情怯”之類的表述。無論生活在哪裡,我都不抱任何指涉“驚喜”和“幸福”的希望。除了在時間節點上,其他方面,鄉村和城市、南京和異地,它們沒有先後、優劣之分。這是一個世界觀的問題,無道理可言。
行李:那寫作對你意味著什麼?
曹寇:總是厭倦,迅速地感到疲憊和勞累,這是我的性格弱點,不積極,不樂觀。對於所謂漫漫人生,我熱衷於“一眼望到頭”的感受。短暫是其真實,漫長的盡是無聊和虛無。惟一安慰我的是,尚可藉寫作排遣這“一眼望不到頭”的困惑。但它是需要窮其一生的事業,而非簡單的愛好。它堅定了我的信念,使我還有那麼一點繼續虛度時日的動力,使我可以延續這無聊和虛無。但我還沒有寫出自己認為的那種“好東西”。在“好東西”面前,我永遠是個屌絲,永遠是個“小混混”,這是我最大的傷心之處。
行李:為什麼要這麼無聊和虛無呢……
曹寇:這跟我的世界觀有關,一個人莫名其妙的來到了這個世界,莫名其妙的做著一些自以為是的事,它們到底是真相還是幻影?
我信任死亡,對活著卻充滿了懷疑。我也經常看到死亡。在八卦洲,我們村子的東邊,有個巨大的墳地,新墳壓舊墳,埋著幾乎半個鄉的死人,包括我的祖父母和父親。在某個層面,這個世界是靜止的,不存在任何新意,活著就是重複死去的人生或重複往生,在此生,也無非日復一日。而我寫東西的基本倫理,是“使我與自己更加相像”,所以你會覺得我的小說涉及無聊。在我這裡,無聊就是我個人的生活境遇,也是生活的品質。就像我喜歡韓東的作品,沒有宏大敘事,都是雞零狗碎,一個人的生活真相無非如此。
更多南京訪談:
行李︱魯敏:在六朝煙水裡野蠻生長
行李|葛亮:歷史走到南京就不願繞行
行李︱葉兆言:南京啊,就是一座空中樓閣
行李︱衛西諦:有如走路的速度【Citywalk系列·電影南京】
文字整理:Daisy
照片提供:曹寇

下一篇:電子票據大揭秘